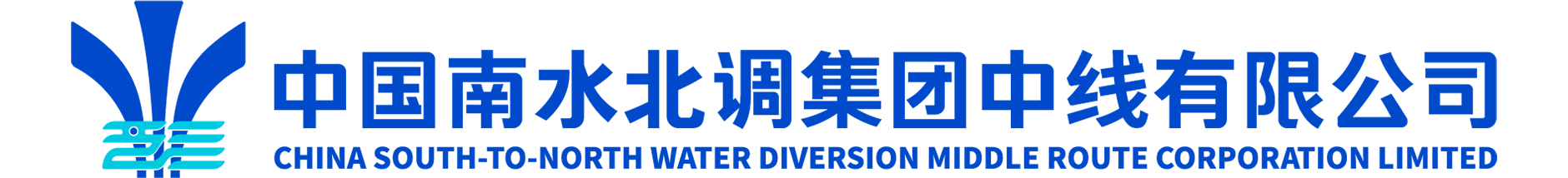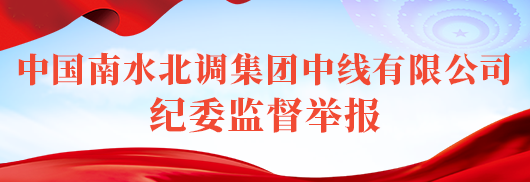磨面感悟
磨面,顾名思义,就是把粮食放在专用设备里,磨制成人们便于食用的粉末或者颗粒状半成品的过程。
这个周末,在老家陪同父亲去邻村磨坊磨了一次面,感悟颇多。
我儿时在峰峰矿区一个农村长大,家乡人一般不说浪费粮食,而是说糟蹋粮食。在老百姓眼里,人要活命,得靠粮食,粮食与人有着过命的交情,而珍惜粮食、敬畏粮食最朴素的观念就是“颗粒归仓,勤俭节约”。
农村人最知种粮苦,都跟粮食亲。记得小时候收麦子,芒种前后是农家人忙断腰的一季。布谷鸟的叫声催着整个村子,“黄了麦子”是一年中最大的担忧,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地里的麦子抢收完。印象中,那时天还黑着,爷爷、父亲、母亲以及姑姑便拎着镰刀,踏着月光下地了。
父亲割麦子快,手持镰刀弯腰揽麦,只听到麦秆遇刃的“嚓嚓”声,一行割完才直起身来擦把汗。父亲说这样割麦,一来少起身,腰就少疼点儿;二来可以少擦汗,不直起来汗就直接顺着眉毛滴到地里了。那时,小学都放麦假,让我们这些孩子也帮着家里麦收。很多年后忆起割麦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金黄的麦浪,交织着滚烫的汗水和弯曲的背脊……收一季麦下来,父亲和母亲都会黑一圈、瘦一圈。一粒麦就是一滴汗珠,一仓黄灿灿的麦子,就是一缸滚烫烫的汗珠。
割完麦子,我和姐姐的任务就是拾麦穗。看着两篓排列整齐的麦穗,姑姑会表扬我们说:“你俩拾的这些麦子,够买3个馍馍了。”这样的表扬,比起那些“长高了”“懂事了”,更让我们开心。拾完麦穗后,还要等着下一轮的玉米播种。
收麦后的第一顿馍,是我们最期待的。蒸馍前,父亲挑水,看火,母亲揉面,做馍,上蒸笼。蒸笼开始变得潮湿,不断冒出麦香味儿时,我的小肚子开始“咕咕”叫,我和姐姐一步不离地守在旁边,等着开笼。母亲心中有数,她说蒸馍的火候要刚刚好,不够火或者蒸过了,都不好吃。她一声“起笼”,笼盖一掀,那叫一个香啊!又大又白的馍馍!
农村人对粮食的态度是三尺黄土般的心思,种粮时那些艰辛的历程,仿佛是在天地之间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。冬去春来,风调雨顺,农人收获着大地的礼物。这饱含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粮食,喂养着人类,一代又一代。而对于一粒粮食来说,从土里到达肚里,才是它的归宿。
从小麦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收割、晾晒、入库、再到磨面,我深刻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,自然不敢浪费。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,不少规矩都是从吃饭而来,比如,吃多少盛多少,碗里不能剩饭;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捡起来,到不了人肚子里,也要到家里喂养的小狗肚子里;放学路上买的煎饼,吃不完一定要带回来。粮食,是农村一家人最可靠的家底。
小时候,我家的上房有好几个缸,里面装的全都是粮食,有谷子、玉米、小麦。过年写对联时,大人们会特意写上“米面满缸”“丰衣足食”等话语,期盼着年年粮食充足,衣食无忧.......
以粮为心,心存敬畏。如今,生活条件富裕了,农忙时节不再去地里捡麦穗。现在的粮食逐年增产,种粮收粮也全部实现机械化,但小时候与粮食的交情,让我更加学会了珍惜。
时代在变,人与粮食的关系没有变。现在因农村土地流转,我家虽然不再种粮了,但看到粮食总是格外亲。对粮食的这份情义,我也一点一点地讲给孩子,并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,也是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——勤俭节约,珍惜粮食。